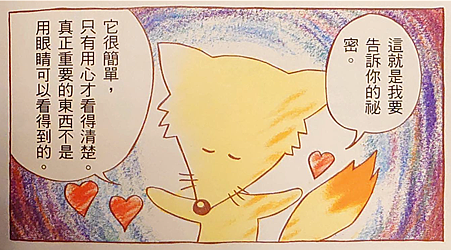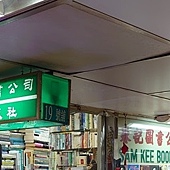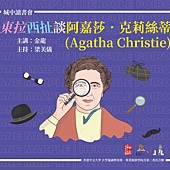At the close of the day, when you kneel to pray,
Will you remember me?
I need help every day, this is why I pray,
Will you remember me?
When you pray, will you pray for me?
For I need His love and His care.
When you pray, will you pray for me?
Will you whisper my name in your prayer?
At the break of the day, when I kneel to pray,
I will remember you.
You need help every day, this is why I pray,
(And) I will remember you.
When I pray, I will pray for you,
For you need His love and His care.
When I pray, I will pray for you,
I will whisper your name in my prayer.
"When You Pray"
Audrey Mieir